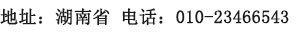我出生在圪崂村,在漆水河畔长大,虽然离开村子已将近40年了,但对家乡的思念魂牵梦绕,难以忘怀!在此,特将对家乡往事的回忆整理成系列作品,今日推出拙作《青草萋萋》,以表达我的乡愁,并留作纪念。
——题记
漆水河从我村环绕流过之二:
青草萋萋
文/李泉
我们这些小时候拔过草、割过草的农村孩子,对草有着特殊的感情。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,但无论是出去旅游,还是漫步于公园或田野,当我看到青草萋萋时,不由得俯下身子,喜爱地抚摸一下小草。心里想,当年自己割草时,若能遇上这么一片草青该有多好啊!于是小时候在田野里拔草、割草的情景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我们农村孩子,从四五岁开始,在大人的带领下,提着小提笼到地里去拔猪草。由于年幼,对草和庄稼分不清,时常把麦苗和菜苗当成草拔回家。
六七岁时,拔草成了家里布置的"任务",但那时的拔草却是一种快乐。每年春节一过,冰雪消融,万物复苏,一望无际的田地里,小麦开始返青。这时,麦地里的野草也随之生长起来,村里的孩子成群结队,去麦地里拔猪草。
在同一个地方,同样是麦田,但不同生产队的地里,其草的生长情况不大一样。上一年对草籽消除较干净,耕种细致的生产队的麦地里,野草则少。所以,我们经常选择"懒汉"生产队、草多的麦地去拔草。
一到地里,小伙伴们自然散开,各自选择地方蹲下,用小铁铲子挖荠菜、萝菲坛坛、麦虎苹、猪兜兜、灰灰菜等草,一把一把地放在提笼里。大约半晌时分,小伙伴们提笼的猪草即将盛满时,耐不住性子的孩子便开始在地里"撒欢"。
于是,大家都放下手中的小铲子,在松软如绿毯的麦田里玩。男孩子一起斗鸡、翻跟头、打车轱辘。女孩子扔沙包、踢毽子,男孩女孩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和丢手绢游戏等。
中午时分,太阳暖洋洋的,小伙伴们玩累了,就把棉外套脱掉,坐在地头玩"狼虫虎豹"(一种类似于象棋对弈,用纸叠成四方形,然后标上动物名字的游戏),女孩子围坐在地上"抓摸儿"(将几个、甚至十几个相当于拇指大小的碎砖块或土块,用手一边上扔下抓,一边念着口嘙)。
大一点的孩子,则用扑克牌通过"比大小点"或"推五龙十点半"的方法进行"赌博",下的"赌注"是一把猪草。结果,手气好"赌赢"的孩子,可以不劳而获,赚满一提笼猪草,"赌输"的孩子提笼里的草所剩无几,因此而不能按时回家吃饭,只能"加班"去拔草。
有一次我赢了一大堆猪草,提笼放不下,就偷偷地在地坎处挖了一个洞,把多余的草埋在里面。第二天把草从坑里刨出来时,许多草已经发黄,只好继续去拔草……
上学以后,随着年龄的增长,拔草成了我们的"天职",每逢星期天或学校放假,我们都要去田地里拔草。当年,由于粮食紧缺,家里养的猪主要吃用谷壳制作的糠,从地里拔的青草,是猪食的重要补充。如果家里养的猪多,拔猪草的活就更加繁重。
七十年代,我家一直靠养猪增加家庭收入,最多时家里养了四头猪。父亲、嫂嫂在生产队上工,哥哥在外村当教师,因此,养猪拔草以母亲为主。
起初,我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拔草,经常由于贪玩,一晌午拔不到半提笼草,为了回家"交差",就把草在河水里淘一下,这时,已经发焉的草叶子即刻变硬,很快澎胀起来,提笼里的草就由多半提笼,虚涨到一提笼。母亲识破了我的"小鬼计",从此以后,节假日便带着我和她一起去拔草。
母亲为了拔草,走遍了村里的田间地头。塬上、河滩,沙地,玉米地、稻田埂、红薯地、树林里都留下了母亲的足迹。
最令我难忘的是暑假期间,入伏以后,玉米已经长到一人多高,母亲领着我到玉米地里去拔草。
为了防止玉米叶子划伤肩膀和胳膊,母亲和我都穿上粗布长袖衬衫,提着笼子和小铲子,早晨天刚亮就进入玉米地里。这时,玉米叶子的露水很快就打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服,浑身冰凉。
我和母亲在玉米陇里穿行,一会儿碰见马齿苋,一会儿找到田旋花,一会儿遇上仁旱菜。母亲手脚麻利,很快就把草拔掉放在提笼里。
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,我和母亲拔草不知走了多少亩地,打湿的衣服暖干了,提笼里的草也增多了。
临近晌午,烈日当空,玉米叶子被阳光晒蔫了,玉米地里成了大蒸笼。我和母亲大汗淋漓,衣服全湿透了,汗水从我的头发稍上滴到干涸的地上,瞬间蒸发。母亲热得眼睛都睁不开,还在坚持着拔草,不把两个提笼拔满坚持不回家。
快到吃午饭时,我和母亲总算拔满了两提笼草,娘俩坐在地头树下休息。我脱下被汗水浸透了衣服,脸颊和脖子被玉米叶子划成了一道道红血丝,伤口和着汗水,像撒了盐一样的痛。
母亲看着我心疼不已,撩起她的衣襟一边抚摸着我的伤痕,一边安慰我:"我娃可怜,从小跟妈受罪。咱好好拔草养猪,等冬天把猪卖了,咱家过年就有钱了,积攒钱供你上学,还要给你订媳妇呢!"
看着母亲黑瘦的面容流着大汗,我哭着说:"妈,我不订媳妇,我要好好上学,将来挣钱养活你!"汗水和着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……
过路的熟人看见我娘俩这么热的天,还在玉米地里拔草,带着不解和指责的口气说:"大嫂,你过日子也太狠心了吧,这么热的天有谁在玉米地里拔草?你不怕把你和娃热出毛病?"这时,我妈无言以对,连忙起身,很无奈地说:"不拔咧、不拔咧,回家!这就回家!"
此刻我突然明白,原来是村里人嫌热,一般不愿意到玉米地里去拔草,我母亲是因为不怕艰难,才去草多的玉米地里拔草。
拔草返回路上,阳光特别刺眼,知了的嘶鸣非常刺耳,母亲又黑又瘦的胳膊挽着二十多斤重的草笼,迈着小脚吃力地走在前面,我提着小草笼无精打采地走在后面,看到母亲被玉米叶子挂乱的发髻和汗水浸透的衣背,我无比心痛、感慨万千……
那时,玉米夹道的田间小路显得更加幽深、曲折而漫长……
从十一二岁能背起背篓开始,割草则是我们沿河流域,农村孩子干的主要农活。每到夏季,漆水河和渭河两岸,莺飞草长,青草萋萋,这是我们割草的好季节。
割草的工具是竹铁制的镰刀,和竹编的背篓。要想会割草首先得学会磨刃片,刃片磨得锋利,镰刀割草又快又省力。其次是要学会往背篓里装草,会装草的,一次可以装七、八十斤,否则,只能装五六十斤。
每年暑假,是我们割草旺季,河滩地里、水田埂上和树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割草的身影……傍晚时分,从渭河滩返回村子的路上,收工的社员、马车、架子车和背草背篓的孩子汇合在一起,从南向北流动,一幅车水马龙的景象!
割草是个力气活,不仅要有连续几个小时、蹲在地上割草的耐力,而且还要有背上超过自身体重的草、走很长路的体力。一个人若想蹲在地上,把几十斤重的背篓背起,必须鼓足浑身力气,靠爆发力站起来。
刚学割草时,由于年少力薄,加上经验不足,不知有多少次,我在背背篓起身时,被压在背篓下面。有一次我被装满草的背篓压在了水田里,头埋入泥水中,差点窒息过去。几经挣扎,最终翻过身子站了起来,当时满脸是泥,浑身湿透,欲哭无泪……即使这样也没人能帮我,自己还得想办法把背篓扶起来,清理一下泥水,穿着湿衣服把草背回家。
好不容易背上背篓,我们中途休息时,一般不把篓背放下。当特别累、背不动背篓需要休息时,只能找个地方,把背篓底放在高处支撑着,人站在低处,歇歇脚。于是,从河滩回村里,道路两边的高坎处,布满了背篓停靠的痕迹,它成了我们割草歇脚的"驿站"。
我们把割的嫩草,一般都交到生产队的饲养室,喂牛和其它牲口。生产队按草的重量,折成工分给我们计报酬。把枝长且又老的草背回家,在家里晒干积攒起来,随后,用架子车把干草卖到养马场,挣的钱给自己交学费、买小人书。
青草割不尽,夏雨催又生。就这样,一个暑假下来,村里的孩子们把河滩的野草割了一茬又一茬。
由于长期在田间干活和割草,开学时,一个个白皙的皮肤变得黝黑黝黑的,身体消瘦了好几圈,背背篓将双肩磨破,有些孩子甚至留下了驼背症状,干活、割草使手掌起了血泡,双手都留下了被镰刀割伤的疤痕。
我手上的两处伤痕至今没有消失,成了割草的永恒记忆……
—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——
作者简介
李泉:笔名山泉,现就职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某研究所,文学爱好者,擅长写作诗歌和散文,用真情实感书写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。有多篇诗文刊发于报刊和网络平台。
往期精彩,敬请浏览——
散文
漆水河从我村环绕流过之一(文/李泉;诵/左瑜)
散文爱字(文/程志海)真情
乐为检察人夕阳添余晖(文/黄振涛)散文
石头河水库环游记(文/陈爱国)散文
龙王沟里一平湖(文/胡汉新)散文
瓜熟蒂落(文/吴妮妮)散文
买瓜(文/张寒)散文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(文/雷密鸽)散文
游千亩荷塘(文/闵选社)
敬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