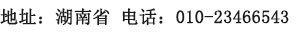三月里的草
庞济韬
山里的草,三月了,还没有长起来。
在山里,草是有声音的。虽然不像梨花、桃花,白似雪,绯如霞,聚焦了好色猎艳的目光,兴奋了采蜜啜芳的蜂蝶,热闹得紧!不过呢,你若是个细心人,管保能听到草丛中有什么声响——那是草长个子的声音。如果有一大片草,碧油油的,那么这声音就更响了。草们攒着劲齐刷刷地长,那声音也是碧油油的了,整齐而清新,是一曲绿色大合唱。
在山里,虽然春天以隆隆的雷声昭告登基,但倒春寒隔三岔五地闹事,好多草因营养不良而不得不放慢了生长的速度。放眼望去,去年的枯草处处可见,新绿就杂在其间,它们一起当风抖动,抖出了一派斑斑驳驳、黄绿相间的山间春光。山坡上,荆棘始终是草的好伙伴。它们叶子还没有长出来,就那么光秃秃地叉开既瘦且硬的手臂,在料峭风中和倒春寒撕扯扭打。地面,一丛丛春草护住了荆棘的脚。大家一起努力,打退倒春寒的进攻。
山里的草,最接充沛的地气。山是大地隆起的肌肉。草扎根于大地雄健的肌肉上,秉天地正气,受日月精华,栉风沐雨,眠云餐露,因此韧性十足,力量惊人。不要问冬天什么时候才走,也不要管春天什么时候真正到来,山里人在阴历中梳理节气、侍弄庄稼、打点生活,不知不觉中鸟雀声声响起,举头一望,千军万马的野草已经悄然催绿了山山岭岭。
在山里,草永远铺不出城里草坪上那样的绿色丝绒毯。它们虽然地位低下,身份卑微,但个性鲜明,相貌各异,该高的高,该矮的矮;该胖的胖,该瘦的瘦;该繁复的繁复,该简约的简约,每一株草都是清清爽爽,素面朝天。它们没有城里的亲戚那么优雅、那么华丽、那么齐整,但很真实、很自在、很健康。我不知道城里那些人工修剪的草的名字,但我却对山里的草的名字稔熟于胸,含羞草、狗尾草、麦麦草、马儿杆草、猪耳朵草……一如我稔熟那些儿时玩伴的名字。
山里的草,蓬蓬勃勃地长。割草的人们将它们扎成束整整齐齐码在背篼里,它们便很骄傲,因为够嫩、够绿,实在是春天的代表。油菜花开了,在春草的映衬下,金子一样的耀眼,一块又一块,一片又一片。猫们、狗们、鸡们,满田坝疯跑,蜜蜂嗡嗡地闹,蝴蝶款款地飞,人的脸被映得亮堂堂的,只想微微地笑。
山里的草,和山里的人难解难分。女人,割牛草,打猪草,天天和草打交道。男人,种田,耕地,累了,坐在草上,吸一支烟,躺在草坡上,用草帽遮住脸,眯一会瞌睡。孩子,拿草编织玩具,在草地上打滚。烧饭时,炊烟里弥漫着柴草的气息。吃饭时,碗里有灰灰菜、苦菜、荠菜。夜里睡觉,身子下面是干谷草,翻个身,草就在下面自言自语。生病了,上山采草熬成药水喝下去,用草的力量和地气击退山里的大病小灾。人走了,深躺在地下沉睡,很快,坟头上就站满了草在深情摇曳。住久了,院坝里长了草,瓦楞上立了草,便是土墙根,也爬满了青苔。有时,你简直分不清,究竟是人像草呢,还是草像人。
如今,很多人离开大山去远方寻梦。人去院空,那些草就来忠实地守着空房子。有的,走了还会回来。有的,永远不会回来了。
只有草,一年年,绿了又黄,黄了又绿,在群山之中无语芬芳。
社长:赵桉平
编委:孙国贤徐栩蒲苇刘丽英赵建琼庞济韬王斌王伟
主办:壁州诗社
协办:深一度文化传媒
麻辣通江传媒
欢迎投稿壁州诗社:mltjcm
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