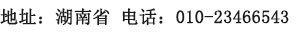割草不等同于打猪草。打猪草的多是儿童,放学没事干,三五结伴去打猪草。因为猪的主食是剩饭剩汤及麸皮,草是点心。说是草,其实大多是菜类,野菜。面条棵、灰灰菜、狗秧子、扫帚苗等,都是人能吃的。
割草,是农民农闲时的一项“副业”。七八月份的田野,正是庄稼疯长的季节,庄稼疯长,草也跟着疯长。那时尚没有除草剂,全靠人工除草,勤快人家的地里草少些,懒人家的地里草能齐腰深。今天去哪块地,割草人整理工具时,心里已经过滤了人选。
割草 的季节是立秋后,农谚说,立秋,挂锄钩,意思是庄稼不用松土或除草了,即使有草,也不是很影响庄稼的生长。这时人们闲了,草也有了质量,不像当初葱绿水灵,一掐一股水,有分量没质量。所以,这个空当,闲人和好草一拍即合,诞生了一个人数还颇为壮观的割草队伍。
割草的工具就是一把锋利的铲子。下地之前,将铲子在磨刀石上来回蹭几下,带着一股子铁锈味就上路了。人们在路上还相互打着招呼,一钻到庄稼地里就不见了人影。
割草不是什么技术活儿,找到一片好草是关键。面对好草,蹲下身子,左手抓草,右手拿铲,双手协调配合,一会就是一篮一箩头。
棉花、大豆、红薯等低矮庄稼地里割草相对会舒服些,能趟着庄稼巡视,哪里有草一目了然。蹲下割草,庄稼才没半截身子。如果是阴天,又有风,算是优质工作环境了。割一会儿,站起来,舒展舒展筋骨。望四野一片碧绿,天空有鸟飞过,附近有牛羊啃青,远处有孩童嬉闹。看一会儿,再蹲下继续割草。但遇到大毒日头天,下蒸上晒,没个遮挡,滋味也不好受。这里是割草季的 战场,之后好草便不再好遇,有进取精神的早就开疆拓土,转移了战场,能在这种地方长期坚守的,多为安于现状的人。
新的草场在哪?玉米地,玉米地里割草,那才真叫受罪。首先你得穿长袖衣服,不然胳膊上会被玉米叶子拉出一道道口子,渍啦啦地疼。在这里找到好草也不容易,好草不是遍地都是,又不能居高临下地瞅,只能在玉米趟里来回钻。但一旦找到好草,会是一大片,不用换地方就能满载而归。
玉米地里割草,最难受的是热,不透风,闷热。还有就是孤独感,没有谁会在玉米地里结伴割草,即使好朋友一块儿钻进了地里,也会分头找草。
傍晚,暮霭起时,散落在四处的割草人就会如约地会聚在路上。有肯下力气的,背一箩头草,光见一堆草挪动,看不见人脸,只看见前后交替的两条腿。由于身肩重负,又急着赶路,人们见面打招呼也显得气短。但打猪草的孩子们依然是奔跑着嬉闹,你怼我一拳,我扫你一腿,篮子里的猪草不时被颠出一两把。
路两旁的杨树叶子,被风吹得哗啦哗啦。村子上空的炊烟已连成了一片,割草人好像闻到了饭香,腿上有了劲。
草有两种用途,一是家养了大牲口,需要青饲料。二是没养牲口的人家,会将青草晒干,等冬天饲料奇缺的时候卖钱。
家有牲口的人,将草割回来后,细细挑拣了,码成一扑,压瓷实放在铡刀边。铡草是两个人的活儿,一人填草一人铡,也不很说话。“卟——咔嚓,卟——咔嚓”,一填一铡,带有声响,很有节奏感。不一会儿,一扑扑的长草蔓,变成了一堆细碎的草节儿。这时,一股特有的青草的芬芳便在农家小院里弥漫开来,就像城市里草坪刚刚刈过的气息。
接下来,将碎草撮到淘草缸里,洗净捞出。等草控干水,倒到牲口槽里,拌上少许的麸皮或玉米面。牲口们已迫不及待,一吞一大嘴,一吞一大嘴,吃得那个香哟,就像嗜荤的人吃到了红烧肉。
没养牲口的人家,会将割回来的青草倒在院子里摊晒。男主人用木杈挑起一扑草,臂弯抖动几下,瓷实的一扑草就均匀地自然散开。一箩头草抖擞完,脚下就成了一片小草原。往往这时,孩子们会一拥而上,在草地上嬉笑打闹,翻跟头打轱辘,滚一身草屑,染一身青草气。
鲜草晒成干草时,拢成一堆,一天加一层,日积月累,成了一个大草垛。冬天,闲人们依在干草垛上晒暖儿,软和,暖和。一冬天了,仍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草香儿。
内容来:闲去记,在此感谢